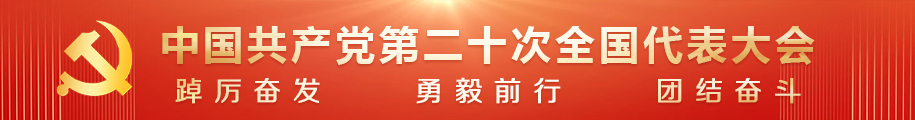成渝地区城镇化路径选择
四川行政学院经济学部 周铁军
内容提要:成渝新型城镇化可以表述为农村人口定居于市辖区与建制镇,在物质、文化与公共福利方面与原城镇人口趋于一致的过程。从世界城市化发展进程来看成渝城镇化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但超大规模城市的虹吸效应、产业支持困境、环境约束、人口结构约束以及城镇化的制度藩篱都构成了成渝城镇化发展的约束性条件。成渝城镇化应坚持政府主导原则、产业城镇一体化原则、城镇化质量原则、新农村建设服从城镇化原则,以城镇化、产业化、信息化三化互动、大力发展绿色生态产业、顺应迁移趋势,完善迁移制为路径选择,实现成渝地区城镇化健康发展。
关键词:城镇化;产业化;路径;公共福利
一、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进程及历史启示
国家统计局2012年1月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1.27%,城镇人口首超农村人口,达到6.9亿人。在这个大背景下,成渝城镇化趋势不可逆转,汲取其他国家的城镇化经验,有利于我们寻找到正确的城镇化道路。
世界各国城镇化进程选择的道路各有特色,按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先后顺序,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代表,这些国家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步调一致。城镇化与工业化积极互动。以1841-1931 年间英国为例,工业化与城镇化相关系数为0.985,法国 1886-1946年间为0.97,瑞典 1870-1940 年间为0.967,整个发达国家为0.997[1]。第二类是拉美国家的城镇化进程。拉美国家的城镇化速度快于工业化速度。农民迅速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后,并没有被其他产业所吸收。游离在稳定的社会生活以外。第三类城镇化进程以成渝为代表。中国率先推动的是区域整体的工业化进程。利用城乡二元结构为工业化提供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诸多限制农村人口城镇流动的政策使成渝城镇化进程远落后于工业化进程。用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衡量,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处于中上等收入国家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4396 美元,但用城镇化率衡量,成渝城镇人口占全社会人口比重只有 49. 95%[2]。
二、成渝城镇化的新旧时代
(一)改革开放后“伪城镇化”进程
数据显示,成渝城镇化水平在中国属于中等偏下水平。即便如此,其中还包含着某些虚假的“城镇化”。一方面,上个世纪90年代,国家重新调整行政规划,许多地、县直接改为市,周边郊区直接成为市区。建制变化、名称变化却没有改变这些周边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达不到城市的水平,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也都没有得到提高。另一方面,成渝地区有大量农民工,他们虽然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由于户籍限制,又不能分享城镇化成果。第三,农村土地囿于政策上的不得流转使得农村人口天然失去了土地交易的收益,这恰恰导致了农村人口与城镇人口在财富上的第一次分野。既便有土地交易也是在政府强制改变土地用途后的间接交易。农民获得的也只是微不足道的补偿,巨大的土地利差还是留在了政府手中。
(二)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学术界与实务界在城镇化的内涵有诸多的争议。但有一些内涵是可以得到一致认同的。城镇化伴随工业化过程进行,不论这种伴随是紧密还是松散。形式上城镇化表现为过去的村民现在居住在城市或城镇。内涵上说,它是人们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公共福利及基础设施城乡差距缩小,直至平等的过程[3]。成渝新型城镇化具体可以表述为农村人口定居与市辖区与建制镇,在物质、文化与公共福利方面与原城镇人口趋于一致的过程。
三、成渝式城镇化贯穿原则
(一)政府主导原则
从世界城镇化历史的角度看,政府在城镇化中所起的作用巨大,尤其是对基础及公共福利方面功不可没。英国于1909 年颁布的《住宅与规划法》是世界上第一部城市规划法律。英国中央政府在城市规划体系中发挥显著的主导作用。西方国家政府由于宪政体制的约束,使得他们的功能只是局限在规划,社会福利等方面。在巨额的投资,全面的拆迁等系统性工程则会显得力不从心。
成渝地区事实上的“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决定了成渝政府绝对的掌控能力。只有政府才能承担起全面长远的社会规划和巨额的建设投入。从短期来看,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型的经济模式还将维系,从推动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政府也必然会对城镇化全力以赴。
(二)产业城镇一体化原则
世界城镇化进程告诉我们,城镇化一定会伴随着产业化,产业化一定会促进城镇化。稍有不同的是城镇化与产业化可能同步也可能不同步。但最朴实的道理在于无论是村民成为市民还是市民成为村民,人们居住在哪里就需要在哪里就业发展。具备产业支撑,才会有持续定居的公民。优化产业布局,打破城乡产业偏见,农村积极地参与到产业结构的转换与升级活动中去。城镇化需要注重为农村配套产业服务,产业项目要立足于对农业富裕人口和转移人口的吸收。产业化为城镇化铺设了一条内生增长的发展路径。(三)城镇化质量原则
“城镇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人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和目的。城镇化改变的不仅仅是人的生存空间,更改善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和道德素质。和谐、乐观、向上的生活方式承载于新型城镇化中,农村转移人口的生存技能会得到提高,生活水平也会有长足进步。城镇化的艰难不完全在于城镇数量的多寡,与人有实质意义的还是城镇化的质量。以城镇化质量为导向,创立城镇化指标考核体制,让转移人口的生活质量的提高看得见,摸得着。城镇化效果可以评估,教训可以总结,经验可以推广。
(四)新农村建设服从城镇化原则
新型城镇化建设不是将所有的村民都变成市民,而是要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要生存空间。农村人口适当转移后,农村人口也会处于一个比较均衡的数量水平。相对这部分农村人口来说,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会相对富足。新农村建设包括发展新产业、建设新村镇、构筑新设施、培育新农民、树立新风尚等方面。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一定程度上会相对集中,农民的增产增收,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农村与城市差距都可以妥善解决。
四、成渝城镇化进程约束条件
(一)超大规模城市的虹吸效应
成渝工业化进程首先伴随的是城市化,而不是城镇化。工业越发展,城市作为载体则越发得到加强。这种加强体现在城市的扩张,城市人口的收入水平提高,城市的发展机会,城市的福利水平等等。成渝的新型城镇化定义为村民在城市或建制镇的生活。因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农村人口会通过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来实现自己的城镇化之梦。在近郊的农村这几乎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农村人口就地转为城镇人口,享受均等城市化待遇。远郊或者落后地区的农村就不一定如此幸运,即使在落后地区实现了城镇化的转移,可能依然存在经济社会水平相对落后的问题,到中心城市或者核心城市寻找机会注定是他们最好的选择。从今天北京、上海、广州不断上涨的房租、房价可以看出这一端倪。远郊或落后地区的村民被中心城市或核心城市汲取,远郊或边远地区的城镇可能又一次沦为空城。
(二)城镇化的产业支持困境
产业和城镇一体化是贯穿整个城镇化的灵魂,但关键问题在于产业发展本身。产业发展瓶颈化、产业转移水平化,是我们在产业问题上挥之不去的梦魇。问题不单存在于城镇化方面,更重要的是整个世界经济都在做这样的徘徊。自信息化浪潮之后,世界第三次产业革命呼之欲出却又迟迟不来。无论是美国债务危机还是欧洲债务危机都说明一个事实,过去的产业发展体系已经为时代所抛弃,钢筋、水泥、汽车不在成为进步的标志。世界要做什么?成渝要做什么?这些问题都悬而未决。城镇化需要依靠怎样的产业持续支撑,其实是个难解之迷。在成渝地区,一些固有的产业不成配比关系,产业链条断裂。新兴产业屡屡尝试但却举步维艰。多晶硅产业、风能产业,生物产业无不如此。在产业发展迷茫的这一大背景下,城镇化又怎能独善其身。
(三)城镇化的环境约束
城镇化必然伴随工业化,这是历史规律。工业化必然伴随污染也是历史必然,无论如何预见,成渝最终还是走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历史老路上去了。英、美、日、巴西、阿根廷等国在城镇化达到加速阶段时都出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情况。日本1960—1970 年城镇化率年均提高约2. 5%,然而空气质量和水质受到巨大的污染。到20世纪 80 年代才基本解决城市环境问题[4]。2014年统计,成渝地区的雾霾天气总数一直全国靠前,漫天雾霾横贯整个四川盆地,空气净化器销售趋于断货。雾霾的成份主要是能源有关的煤灰,汽车尾气和建筑粉尘等。雾霭的致命性已为专家所一致认同。这其实也宣告了成渝高耗能发展模式的终结,成渝经济发展的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趋于极限,若城镇化不能改变发展模式,成渝所有的经济与社会成就都会因为环境约束而毁于一旦。
(四)人口结构约束城镇化进程
就地城镇化是城镇化最好的结局。成渝的城镇化进程伴随着工业化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过程,这注定异地城镇化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外来人口在异地打拼中,或把握机遇实现了异地的农转非。更多的则是在异地颠沛流离。奉献了热情与青春换回的则是这块土地的漠然与离弃,其实原因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并不属于这块土地,不能享受打工地的医疗教育与养老和其他福利。人口输入地在提供公共服务时,也没有考虑到外来人口的需求。这样又必将导致整体上公共服务的不足。打工者终将老去,他们在35岁-40岁后被迫放弃工作或返乡。这样的迁徙具备了城镇化的形式却无法具备城镇化的实质,那就是生存与生活的均等化,物质与文化的均等化。
(五)城镇化的制度藩篱
城镇化就是消除农村与城镇的制度壁垒、福利壁垒、文化壁垒。现行制度下,这些壁垒造成了农村与城镇的巨大鸿沟。城镇土地可以商业化流转,农村土地不能够流转,因此农民不能够享有资产性收入。人口的流动性加剧了社会保障方面实质的不平等,农村的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就业培训制度等都与城镇形成鲜明的对比。农村人口要成为城镇人口,需要的就是打破制度的藩篱,多渠道地增加农民收入,改变收入水平、消费水平进而促进农业产业化。现有的城镇制度使城镇在扩张过程中不注重农民的固有权益,经济补偿不合理,也未对离开土地的农民作出制度上的安排。
五、成渝城镇化进程的路径选择
(一)引导规模化城市集群形成
城镇化的向上提升就是城市群的形成。规模各异,大小不一的城市群以其广阔的发展空间吸纳着来自各地的村民。城市群的出现还分散了核心城市的人口及公共服务压力。城市群间可以形成不同城市的差异化定位,不但可以避免城市间的恶性竞争,还可以做到优势互补。城市群的形成体现的是集约型的城镇化思路,把产业发展、环境保护、人口转移都放在一个相对集中的空间。这样释放出的耕地将有所增加,缓解城镇化发展所带来的耕地紧张问题。
(二)城镇化、产业化、信息化三化互动
核心城市近郊,希望派生出能够服务于中心的现代服务业,现代安全的农业等等。资源产出地则会立足于资源的增值工业,进而提高从业村民的收入水平。近工业区的城镇则希望通过为工业区提高劳动力以及第三产业的服务业来发展。因地制宜、个性化发展是产业与城镇共生的基本前提。但是当前的产业化与城镇化都是在信息化这一世界背景下进行的,信息化要求产业化线上线下互动一体,信息化要求城镇化中蕴含智能城镇软硬设施。与此同时,信息化会使产业发展更具前瞻性和科学性,使城镇化变得与世界同步发展。
(三)大力发展绿色生态产业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将绿色生态产业做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绿色生态产业包括循环农业,循环工业等。对于城镇化的转入者而言,嵌入绿色生态产业不但是自身经济收入的要求,同时也能更好履行人作为自然之子所应尽的义务。休闲农业、观光农业、有机农业等都在以更具魅力的形式丰富着绿色生态产业的内涵。
(四)顺应迁移趋势,完善迁移制度
人口作为基础性的市场要素,一经市场调配就必然产生出活跃的流动性。制度性障碍撕裂着这一迁移。要顺利实现城镇化目标就是要使人口自由的流动起来,即包括从城市到农村的迁移,也包括从农村向城镇的迁移。逐步取消城镇户籍上所承载的福利差距,在住房价格、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方面实现城镇人口的一体化,在此基础上提高社会保障层次,促进人口流动的更优化。
.png?20211108)